村庄公共性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分析: 基于江西省调查数据
The Impact of Village Publicness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Jiangxi Province Survey Data
-
摘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是形成长效人居环境管护机制的关键。基于江西省1 045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采用二元Logit模型、PSM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 分析村庄公共性、公共精神认同及公共规则认同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村庄公共性越高, 农户越会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相比较高的公共精神认同, 较高的公共规则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 村庄公共性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 包括信任效应和互惠效应, 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异质性研究发现, 对村庄有文化中心和环境整洁认知高的农户而言, 提高村庄公共性能显著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从不同村庄类型来看, 对中青年人口密集型村庄和低收入村庄而言, 村庄公共性越高,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越积极。同时, 公共精神认同和公共规则认同对于不同类型村庄的影响存在差异。Abstract: Enhancing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s a pivotal task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s the key to forming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for manag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Using micro survey data of 1045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 this study employs the binary Logit mode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examine Farmers' behavior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illage publicness, public spiritual identity, and public rule ident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greater degree of village publicnes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Compared to a higher public spiritual identity, a stronger public rule identity exerts a mor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iving environment activities. In addition, village publicness facilitates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by augment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which includes enhanced trust and reciprocity effe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for farmers residing in villages with cultural centers and hig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cleanliness, enhancements in village public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ir involvement in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village types, in densely populated and low-income villages with a predominance of middle-aged and younger residents, a higher degree of village publicnes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farmer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effort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spiritual identity and public rule identity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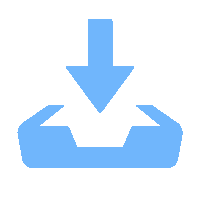 下载:
下载: